一、喪葬習(xí)俗與藏醫(yī)解剖學(xué)的發(fā)展
藏族人死后,因經(jīng)濟(jì)和社會(huì)地位不同,而選擇不同的葬法。其葬法共分天葬、水葬、土葬和墓葬等種。大部分普通人的葬法是天葬,至今仍然盛行。但據(jù)有關(guān)文獻(xiàn)載在遠(yuǎn)古時(shí)期,藏族先民在土葬或墓葬中盛行斷尸葬和二次葬。斷尸葬就是將尸體割成幾段,再行掩埋。二次葬就是對(duì)死者的尸體和遺骨分別進(jìn)行兩次或兩次以上的處理。按吐蕃王朝時(shí)期的文獻(xiàn),二次葬常見(jiàn)的程序是人死后對(duì)尸體進(jìn)行剝皮、分解等解剖處理。掩埋起來(lái),過(guò)一段時(shí)間再挖出來(lái),重新埋葬。盡管它們也是受宗教觀(guān)念支配的產(chǎn)物,但在客觀(guān)上促使藏族先民們對(duì)人體的構(gòu)造有了客觀(guān)的認(rèn)識(shí)。[①]公元七世紀(jì)紀(jì),佛教正式傳人吐蕃,對(duì)西藏的宗教、政治、文化等諸方面都產(chǎn)生了較大的影響。這一時(shí)期,藏民族選擇了天葬,藏民族的天葬習(xí)俗對(duì)藏醫(yī)、解剖學(xué)家實(shí)地觀(guān)察人體組織結(jié)構(gòu)帶來(lái)了方便,大量的經(jīng)常性的尸體解剖使藏醫(yī)學(xué)家很早就對(duì)人體結(jié)構(gòu)有了較為正確的認(rèn)識(shí)。
另?yè)?jù)考占工作者在西藏的考占研究證實(shí),藏族先民在距今約余年就有“穿顱骨術(shù)。” 據(jù)宗喀· 漾正岡布在《史前藏醫(yī)發(fā)展線(xiàn)索研究》一文中提供的材料在三個(gè)墓葬中分別發(fā)現(xiàn)了三例佩帶圓孔的顱骨。這三例為中、老年男性顱骨, 穿孔分別在顱骨左、右側(cè)頂部和顱枕骨左側(cè)。直徑分別為13毫米、10毫米、10毫米, 且孔緣光潔招齊、無(wú)分折、骨質(zhì)增生痕跡, 極像鉆旋成的孔洞。文中還論述說(shuō)根據(jù)圓孔的部位比較定 孔徑不很大等綜合判斷,它們當(dāng)時(shí)是有意用石鉆旋出的, 是當(dāng)時(shí)施行的頗為流行的種穿顱術(shù)留下的產(chǎn)物。特別是從第一例顱骨圓孔周緣有炎癥和新生份芽痕跡的情況看,這種危險(xiǎn)的令人驚訝的手術(shù)并不都立即置人于死地。這種帶有鉆孔的顱骨在法國(guó)、西班牙、德國(guó)、俄羅斯等國(guó)的新石器時(shí)代的遺址中也曾被大最發(fā)現(xiàn)。“有人對(duì)施行這種手術(shù)的用盤(pán)的解釋是當(dāng)顱骨損傷以后, 骨碎片壓在大腦的一定部位并引起痙孿。或由癲狂或不堪忍受的頭痛突然發(fā)作。在顱骨打個(gè)洞, 以便給在顱膠中作祟的‘精靈’ 提供條逸出的通道。”作者說(shuō)這種手術(shù)是由類(lèi)似巫醫(yī)的專(zhuān)門(mén)職業(yè)者施行的,并認(rèn)為穿顱術(shù)是吐蕃史前文化與包括歐洲在內(nèi)的其他史前文化進(jìn)行過(guò)廣泛的交流。[②]穿顱術(shù)在吐蕃史前期的存在也說(shuō)明藏族先民早已具備一定的解剖學(xué)或人體學(xué)知識(shí)。
藏族的喪葬習(xí)俗, 早期的斷尸葬,尤其是解體二次葬、天葬,以及史前的穿顱術(shù), 無(wú)疑為后來(lái)的藏醫(yī)解制學(xué)的發(fā)展奠定了基礎(chǔ)。
醫(yī)學(xué)科學(xué)的發(fā)展離不開(kāi)解剖學(xué)、生理學(xué)的研究, 藏醫(yī)學(xué)的發(fā)展亦不例外。8世紀(jì)初,藏醫(yī)就有關(guān)于人體解剖的記載,這時(shí)期吐蕃王室侍醫(yī)比吉· 占巴希拉編繪有《尸體部分》及《活體及尸體測(cè)量》二書(shū)。[③] 8世紀(jì)中葉他還譯出《醫(yī)學(xué)寶鑒》、《尸體圖鑒》等朽。另外, 8世紀(jì)上半葉著成的《月藥診》也對(duì)人體生理功能和胚胎形成,人體骨骼構(gòu)造,人體的測(cè)量及五臟六腑等內(nèi)容作過(guò)論述。8世紀(jì)半葉,著名藏醫(yī)家宇妥· 寧瑪云丹貢布編著的《四部醫(yī)典》中,對(duì)人體解剖生理及機(jī)能作了詳細(xì)論述。《四部醫(yī)典·論說(shuō)醫(yī)典》第四章生理喻示有“骨骼用量類(lèi)系二十三,其中脊椎骨節(jié)共二十八,肋骨數(shù)量共計(jì)二十四,牙齒數(shù)量共計(jì)三十二,全身骨骼三百六十塊……”等的詳細(xì)記載。第三章身體比象論述道“肌膚如同屋表抹泥漿”,“感官五竅恰似開(kāi)窗戶(hù),頭蓋顱骨屋頂土了瓦”,“胸幅上下走廊有仁下”,“心臟如同國(guó)君正危坐,肺五母葉左右肺為二葉、三葉就是五大臣”,“三木賽生殖器如同一寶庫(kù),胃可消食屋內(nèi)有鍋灶,膀膚猶如缸內(nèi)滿(mǎn)了水,下部?jī)砷T(mén)指肛門(mén)、尿道如同出水洞”等等。藏醫(yī)對(duì)人體各器官富有哲理性的比象,較好地論述了藏醫(yī)解剖學(xué)對(duì)人體各系統(tǒng)功能的認(rèn)識(shí)。尤其是《四部醫(yī)典·論說(shuō)醫(yī)典》第二章身體形成顯示了藏醫(yī)學(xué)家豐富的人體解剖學(xué)知識(shí),他們認(rèn)識(shí)到婦女懷孕后胚胎要經(jīng)過(guò)周的發(fā)育過(guò)程, 并認(rèn)為主要器官塑造期是周以后,科學(xué)論述了妊娠早期是胚胎組織器官分化、形成、發(fā)育的重要時(shí)期,是受精卵開(kāi)始重演人類(lèi)進(jìn)化史的劇烈演進(jìn)期, 其間要經(jīng)歷“魚(yú)期、龜期、豬期”三個(gè)不同的階段, 形象地描述了人體在胚胎時(shí)期重演人類(lèi)經(jīng)歷水生動(dòng)物、爬行動(dòng)物和哺乳動(dòng)物三個(gè)不同進(jìn)化階段的歷史。這與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的觀(guān)點(diǎn)是基本一致的。宇妥·云丹貢布提出的這一人體胚胎發(fā)育進(jìn)化次序, 較之法國(guó)人拉馬克(J.B.Lamark 1744-1829)到年才開(kāi)始明確提出的人類(lèi)進(jìn)化程序約早一千年,也比15世紀(jì)“Leonardo Da Vinci正確地描繪了妊娠子宮及其中的胎、胎膜的解剖所見(jiàn)”[④] 早了近600多年。因此, 這是宇妥· 云丹貢布對(duì)世界生物學(xué)界、人體生理學(xué)所作出的一項(xiàng)大貢獻(xiàn)。這一章還指出“胎兒發(fā)育其臍帶上,子宮左右兩脈通臍帶”, 這種見(jiàn)解比意大利醫(yī)學(xué)家提出的“胎兒山純凈完美的血液通過(guò)臍靜營(yíng)養(yǎng)”的觀(guān)點(diǎn)早800年[⑤]。可見(jiàn),當(dāng)時(shí)的藏醫(yī)人體解剖學(xué)已有相當(dāng)?shù)乃?在胚胎學(xué)領(lǐng)域里濘二世界領(lǐng)先地位,從理論的高度豐富和發(fā)展了藏醫(yī)人體解剖學(xué)。這時(shí)的藏醫(yī)人體解剖學(xué)還對(duì)人體址管有了詳細(xì)的記述,明確區(qū)分了動(dòng)脈和靜脈,尤其知道僥動(dòng)脈的位置,作為切脈辯病的部位。
約在公元12世紀(jì), 被譽(yù)為“凡間藥王”的宇妥· 薩馬云丹貢布,在傳講《四部醫(yī)典》時(shí),曾親自繪制接骨圖畫(huà),并編纂《臟腑解剖圖》[⑥]一部。公元世紀(jì),薩迦王朝名醫(yī)昌狄· 班旦措古又編寫(xiě)了《解剖明燈》[⑦]。17世紀(jì)末繪成的幅藏醫(yī)彩色系列掛圖更說(shuō)明藏醫(yī)學(xué)家對(duì)人體解剖學(xué)有更進(jìn)一步的認(rèn)識(shí)。如傳統(tǒng)的解剖形態(tài)圖由于受宗教觀(guān)點(diǎn)影響,將心臟畫(huà)在胸部正中,以心尖向仁,內(nèi)臟器官的形態(tài)和位置亦多失真。畫(huà)師洛扎· 且增努布在繪制人體臟腑解剖形態(tài)圖時(shí),依據(jù)尸體解剖的實(shí)際情況,將親眼觀(guān)察到的尸體內(nèi)臟形態(tài)和位置,如實(shí)地加以繪制,如將心臟繪在人體胸腔中間偏左的位置心尖朝向左下方,并且對(duì)氣管與肺、腹腔內(nèi)各臟器的解剖位置及形狀的描繪也與實(shí)際情況比較符合, 具有重要的科學(xué)意義。
另外, 藏醫(yī)發(fā)展史上的許多醫(yī)學(xué)著作如《醫(yī)學(xué)理論十八品》宇妥· 云丹貢布著、《續(xù)論》香巴· 桑丹欽布著、《千金舍利》蘇仁· 娘尼多吉著、《藍(lán)毗達(dá)及其配方》第司· 桑杰加措著等的撰述,除與藏醫(yī)學(xué)豐富的醫(yī)療實(shí)踐活動(dòng)有關(guān)外, 尚與醫(yī)家勇敢地拿起解剖刀獲得人體解剖知識(shí)有關(guān)。如著名的洛桑· 倫巴是一位高級(jí)藏醫(yī)師, 這一與他年輕時(shí)就跟著“多不丹”( 藏語(yǔ)天葬師)到天葬臺(tái)學(xué)習(xí)人體解剖有關(guān)。經(jīng)過(guò)日積月累的勤奮學(xué)習(xí),他能夠通過(guò)解剖尸體,檢查各個(gè)器官, 可以立即判斷死因。
二、藏醫(yī)對(duì)人體解剖學(xué)的科學(xué)認(rèn)識(shí)
公元8世紀(jì)是藏醫(yī)學(xué)突飛猛進(jìn)的發(fā)展時(shí)期,特別是宇妥· 云丹貢布等編著完成的《四部醫(yī)典》代表了古藏醫(yī)最高水平,這時(shí)期藏醫(yī)學(xué)家對(duì)人體結(jié)構(gòu)進(jìn)行了系統(tǒng)研究,終于從宏觀(guān)到微觀(guān)積累了系統(tǒng)的人體解剖學(xué)知識(shí),對(duì)人體各系統(tǒng)有了較為科學(xué)的認(rèn)識(shí), 內(nèi)容大致如下。
藏醫(yī)解剖學(xué)對(duì)運(yùn)動(dòng)系統(tǒng)的骨骼描述很細(xì),認(rèn)為人體有塊360骨:即顱骨4塊, 頭背骨8塊, 頸背骨2塊, 齒骨(牙齒)32塊, 齒窩骨32塊, 鎖骨2塊, 脊椎骨28塊, 胸骨15塊, 肋骨24塊, 小肋骨2塊, 小背骨1塊, 髓骨2塊, 臂骨6塊(肩2、肘2、腕2) 手骨50塊, 小腿骨70塊, 指甲及趾骨60塊, 指甲及趾骨窩骨20塊。藏醫(yī)對(duì)人體骨骼的描繪基本正確,如對(duì)椎骨計(jì)數(shù)與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大致相同,與脊椎構(gòu)成的根肋骨與現(xiàn)代解剖學(xué)的記載也是一致的。藏醫(yī)對(duì)牙齒計(jì)數(shù)為32顆,與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計(jì)數(shù)一致,并指出:前12顆牙齒用于語(yǔ)言, 后20顆牙齒用于咀嚼, 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同樣認(rèn)為牙齒是咀嚼器官, 還可影響語(yǔ)言發(fā)音。藏醫(yī)將人體骨骼總數(shù)計(jì)為塊, 這一與現(xiàn)代解剖學(xué)的206塊相比約多出百多塊,究其原因,是藏醫(yī)解剖學(xué)家將牙齒、齒窩骨、指甲、趾甲及窩自等均包括在骨骼內(nèi)。這雖與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解剖學(xué)有一定出入,但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條件下,不能不說(shuō)是對(duì)人體科學(xué)認(rèn)識(shí)的一種進(jìn)步。
藏醫(yī)對(duì)骨與骨構(gòu)成的關(guān)竹認(rèn)為人的全身共有四肢大關(guān)節(jié)12個(gè), 這12個(gè)大關(guān)節(jié)分別為成對(duì)的肩關(guān)節(jié)、肘關(guān)節(jié)、腕關(guān)節(jié)、骸關(guān)節(jié)、躁關(guān)節(jié), 以及小關(guān)節(jié)21處, 韌帶16處。藏醫(yī)學(xué)除對(duì)骨、關(guān)節(jié)做了精確的解剖外,還對(duì)頭發(fā)、汗毛孔也作了較為詳細(x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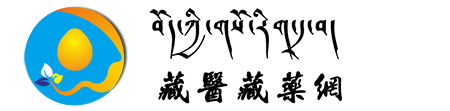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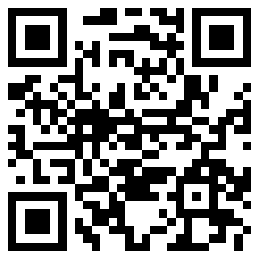
 青公網(wǎng)安備 63010202000369號(hào)
青公網(wǎng)安備 63010202000369號(hào)